然而,就是这样迥然相异的两个人,在生活中却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,虽说彼此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大不相同。没有嫌弃,也没有嫉妒,有的仅是对对方优长之处的相互欣赏与理解。如果说友谊往往脱不了功利性的彼此予取,但在卡利内奇和霍里的友谊当中,我们能够看见的却只有交往本身的愉悦。这一友谊的秘密,即在于他们的平等相待吧。
要是把卡利内奇和霍里放在一起比较,我们也还会有一个发现,那就是等级身份的变换问题。也就是说,在某种程度上,地主及贫农之间的差异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,它还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。霍里虽是一个佃农,可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勤劳,他使得全家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。他委实有能力赎回自己的自由之身,甚至有可能购置土地,进而摇身一变为地主。只是,霍里没有这样做。
为何没有这样做?霍里对屠格涅夫给出了这样的解释:“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,凡是没有胡子的人,就都管得着霍里了。”所谓没有胡子的人,即指当时被官方禁止蓄须的权势者。简单一句话,道出的却是霍里的深谋和远虑:摆脱掉一个主人,结果会换来更多的主人,这样的自由不要也罢。
关键的一点是,霍里很了解他的主人,这个主人待他们也很好,况且交租对他来说又不是个问题。因此,霍里有理由知足常乐。从他这里,我们也能知道,地主及其佃农的关系,亦非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般千篇一律的紧张。屠格涅夫对于一个地主的间接涉及,可以有效还原我们对地主老财妖魔化的历史想象。
而从卡利内奇跟霍里关于主人的争论中,我们看到的同样是前者对于主人的真心维护。不过,即便如此,我们仍不能否认个中存在的剥削实质。这种剥削正是政治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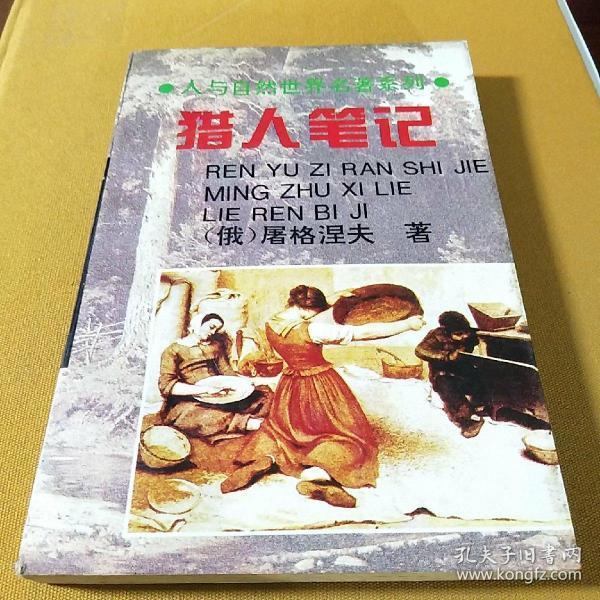
在该篇的尾声处,屠格涅夫用貌似漫不经心的一笔,刻画出了卡利内奇作为一个自然之子的神奇——望着初升的晚霞,屠格涅夫说“明天准是好天气了”,而卡利内奇却说“不,要下雨了,因为那边的鸭子在泼水,而且草的气息特别浓”。无疑,卡利内奇是更值得我们信任的。
叶尔莫莱(《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》)是又一个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农民,他随同屠格涅夫打猎,所以在《猎人笔记》中出现的次数最多。他性格相当古怪,一无所有却无忧无虑,居无定所其实有家。他没头没脑,浑浑噩噩,是别人眼里的废物,可又有着过人的生存技能,是个极有天赋的猎手。他对别人永远充满善意和谦卑,而对妻子却始终是残酷无情,毫不关心她的死活。叶尔莫莱的凶相除了会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毕露,还会在被他打伤的猎物面前毕露,所以屠格涅夫说“我不喜欢他把打伤的鸟咬死时脸上的表情”。
虽说叶尔莫莱古怪得可以,实际上却一点也不复杂。要定义像他这样的人,只需“弱者”二字。弱者的本性即是依赖和索取,他们甘愿忍受强者的欺凌,然后再将怨恨发泄在比自己更弱小的生命身上。对于强者,弱者唯有屈从,从他们那里,弱者习得的仅是压迫和凶残。《总管》里的索夫龙、《事务所》里的尼古拉·叶列梅伊奇等,也统统属于这种仗势欺人的弱者,即便他们看起来要比叶尔莫莱强大得多。简言之,弱者从来就不具备爱的能力。因此,我们无以指望从弱者那里获取给予或拯救。对于弱者,仅有鲁迅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要用我们爱的启蒙使其成为强大者。施舍式的关怀只能让弱者继续沉沦于弱者的处境,而这绝非对于弱者的真正关怀。
《猎人笔记》中的农民基本都是这样的弱者,只是在性情上与叶尔莫莱不尽相同罢了。屠格涅夫在描写他们时,由于秉持着尽可能平等的姿态,故而有了最大限度的冷静。毫无疑问,他是同情他们的,但他也深知,廉价的情感流露或者随意的谴责并不能改变什么,只不过换得的是自我的心理安慰,以及这些不幸者的加倍自怜。有鉴于此,屠格涅夫宁愿不动声色地去书写他们,借助他们的客观呈现启示着我们。





